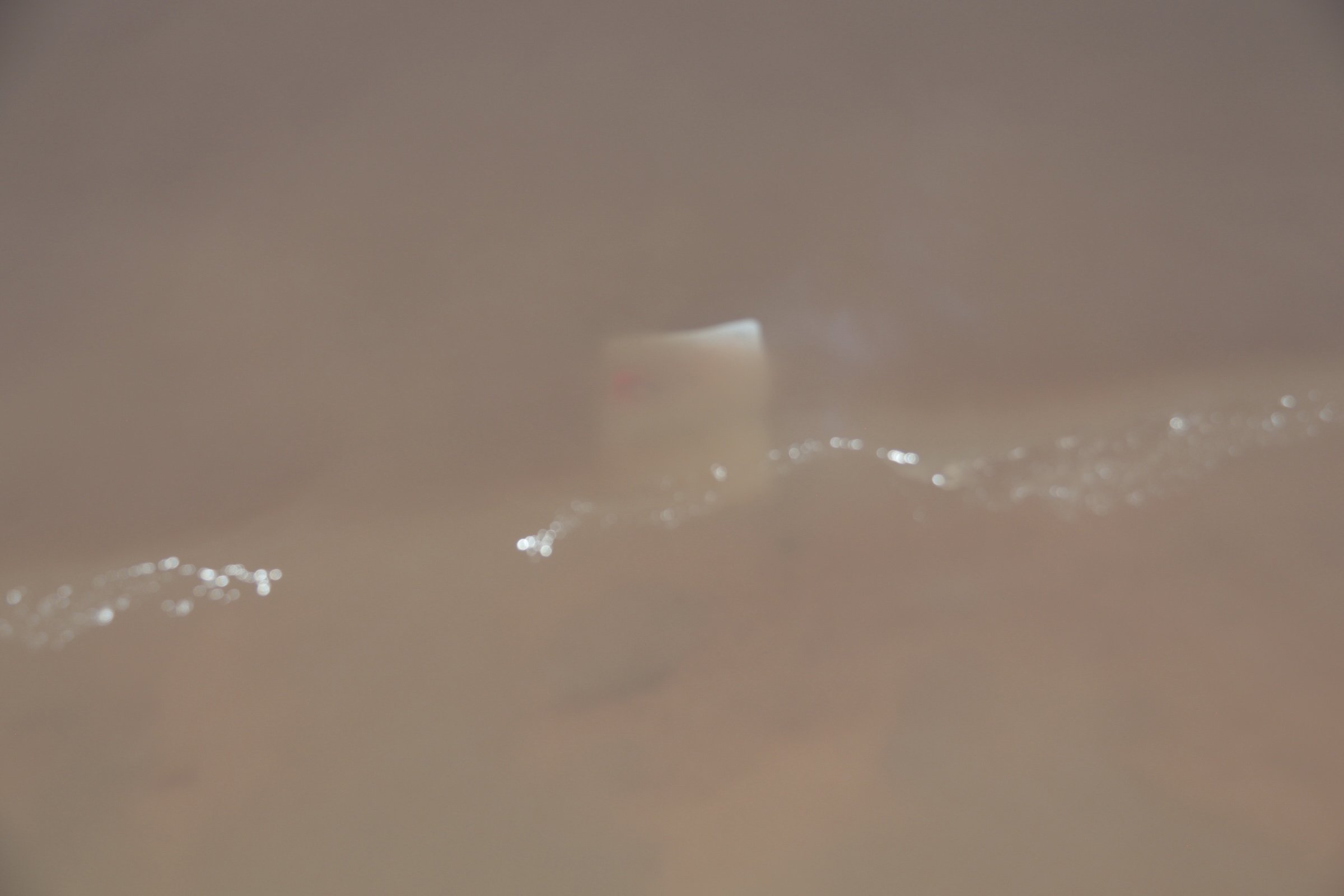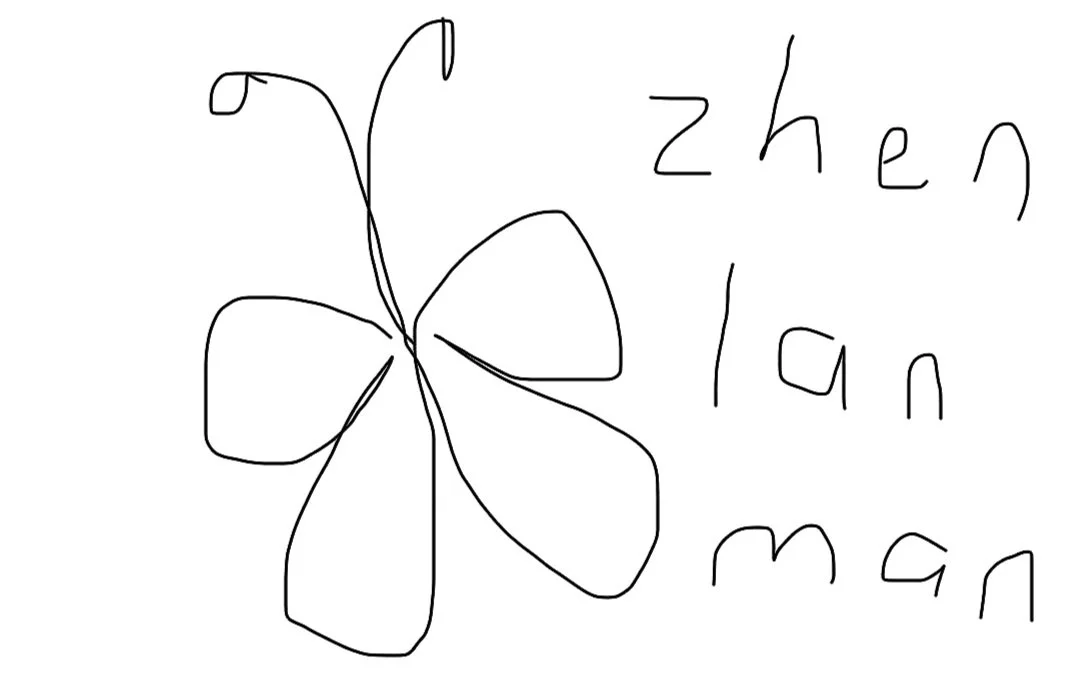大学毕业前,我在学校的档案室里看到一排排整齐摆放的档案,随着时间的推移,它们不断累积、变厚,仿佛在生长,拥有了自己的生命。而在这些纸张和记录的堆叠之下,个体的身份被定义、被确认,甚至在某种程度上,档案成为了个体的替身。
如果我要证明自己存在,我需要出生证明、身份证、户口本;如果我要证明自己接受过教育,我需要录取通知书、毕业证、成绩单;如果我要证明自己拥有一段长期的关系,一张结婚证书便成为法律上的认证。这些档案在塑造我的同时,也在定义我的社会身份。它们不仅记录了我的过去,也成为了“我”的另一种存在形式。某种程度上,它们比我的肉身更具有“合法性”——我的生平被它们所存档,我的社会身份被它们所承认,那么,当这些档案消失,我是否才能真正“活着”?
米歇尔·福柯(Michel Foucault)在权力与知识的讨论中指出,档案不仅是信息的存储工具,更是权力运作的机制。它决定了哪些信息被记录,哪些身份被合法化,而哪些则被忽视、遗忘。雅克·德里达(Jacques Derrida)在《档案热》(Archive Fever)中进一步提出,档案既是记忆的存储,也是遗忘的工具——当某些信息被归档,另一些信息便被抹去。这种“被选择性记录”的机制,使档案不仅仅是对个体的证明,更是对个体的塑造。
另一方面,罗兰·巴特(Roland Barthes)在《明室》中指出,照片的本质是“时间的冻结”,它既证明了过去的存在,也意味着死亡的开始。同样地,档案也具有这种悖论性——它记录个体的生命轨迹,却也让个体被“固定”在文件之中,成为静态的符号。这让我想到中国传统祭祀中的“纸马”:它并不是真正的马,但在仪式的语境下,它代替了马的功能,成为亡者世界的坐骑。同样地,档案并不等于真实的个体,但它在社会制度中代替了个体成为存在的凭证。
我的摄影作品希望探讨这种身份的“被归档”以及档案对个体存在的象征性塑造。通过将档案与身体、影像、纸张、火焰等元素结合,我试图思考:如果档案是个体身份的替代物,那么当它们消失,我们是否才能从被定义中解脱?档案的局限性是否构成了一种“审美误差”,使得真实的个体与被记录的身份之间永远存在偏差?在数字化时代,档案如何从实体变为数据,而个体的身份又如何在被归档的同时,逐渐丧失其独特性?
在当代信息社会,我们的存在越来越依赖于档案系统,而这一系统既给予我们身份,也限制了我们的流动性。我希望通过影像语言,探索档案如何成为个体身份的“第二生命”,以及它如何在权力、记忆、死亡之间构建起一座隐形的桥梁。